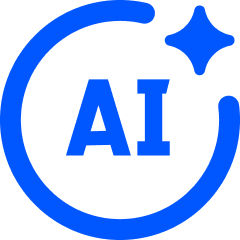华尔街教父、欧央行行长与历史学家激辩:“AI、关税和地缘”将把世界拖向“1930”?
达沃斯论坛上,拉加德、格里芬、芬克和图兹等全球金融领袖警告,当前“技术繁荣+财政扩张+地缘分裂”的格局与1920年代大萧条前夜惊人相似。AI虽非泡沫,但资本门槛极高,将加剧K型分化,仅巨头受益。政府鲁莽支出和关税上升构成系统性风险,威胁市场稳定。数据与能源的碎片化阻碍AI扩展,央行独立性面临政治压力,呼吁最低限度的全球合作以避免历史重演。
作者:龙玥,华尔街见闻
-
历史镜像:欧央行行长拉加德与历史学家Adam Tooze 警告,当前的“技术繁荣+贸易保护+地缘政治分裂”与 1920 年代走向 1930 年代大萧条的路径存在惊人相似。
-
债务危机:城堡证券创始人Ken Griffin抨击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的“鲁莽支出”是当前市场的最大威胁,而非私人资本市场。“所有政府都在超支,几乎毫无例外。”
-
AI并非泡沫但K型分化: 贝莱德CEO、“华尔街教父”Larry Fink 认为 AI 不是泡沫,但会导致“赢家通吃”,拥有规模和数据的巨头(如沃尔玛)将碾压对手。拉加德透露训练一个前沿模型需 10 亿美元,Griffin 预计今年美国数据中心资本支出高达 6000 亿美元。
-
关税与碎片化威胁AI扩展: 欧央行行长拉加德警告,地缘政治分裂和保护主义将阻碍 AI 所需的数据流动和能源获取,导致效率下降。
-
关税代价:拉加德指出欧美关税正从 2% 向 15% 攀升;Griffin 警告关税实际上是向美国消费者和企业征收的累退税,并可能滋生裙带资本主义,扼杀中小企业活力。
-
央行独立性:面对政治压力,拉加德重申央行独立性的重要性,强调财政整顿不能依赖央行“兜底”。

图:从左到右依次为达沃斯主持人安德鲁、贝莱德CEO拉里·芬克、城堡证券创始人肯·格里芬、著名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兹、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
达沃斯寒风中,全球顶级金融权势人物发出警告:政府财政失控与地缘政治的分裂可能正在抵消AI带来的生产力红利。
在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次日的重磅小组讨论中,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CEO、“华尔街教父”拉里·芬克(Larry Fink,管理14万亿美元资产)、最成功的对冲基金之一城堡证券创始人肯·格里芬(Ken Griffin,管理650亿美元资产)、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以及著名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兹(Adam Tooze)齐聚一堂。
在这场被Griffin戏称为“末日与阴霾(gloom and doom)”的讨论中,嘉宾们深刻剖析了 AI 技术爆炸、飙升的主权债务以及地缘政治碎片化,如何将全球经济推向一个危险的、“酷似 1929 年前夕”的十字路口——那个在技术狂欢后走向大萧条的时代。
拒绝“重复”历史,但警惕“押韵”
“马克·吐温说过,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Adam Tooze在开场直指核心。他指出,当前的2020年代与100年前的1920年代有着惊人的相似:彼时是电气化和福特流水线的技术爆发,今天是AI的狂飙突进;彼时是美元霸权的崛起,今天是美元体系的承压。
最令人不安的平行线在于“政治的失败”。Tooze警告,1920年代人们试图用技术和金融来掩盖政治上的裂痕,这种“由于政治想象力匮乏而过度依赖金钱”的模式最终导致了体系的崩塌。
拉加德对此表示赞同。她补充道,1920年代全球贸易占GDP的比重在几年内从21%暴跌至14%,而今天,尽管尚未发生雪崩,但在地缘政治碎片化和关税壁垒的冲击下,全球贸易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压力。她警告称,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全球合作,AI所需的“规模效应”将被割裂的市场扼杀。
财政“鲁莽”:真正的系统性风险
关于当前市场风险的根源,城堡证券的掌门人Ken Griffin给出了犀利的判断。
“这是一个关于鲁莽的故事,但并非私人资本市场的鲁莽,而是各国政府支出的鲁莽。”Griffin直言不讳地指出,与1929年私人部门杠杆过高不同,2026年的核心风险在于政府毫无节制的开支。“所有政府都在超支,几乎毫无例外。”他警告称,这种财政上的放纵正在威胁市场的根基。
目前美国国债已高达 38 万亿美元。Griffin 质疑,华盛顿寄希望于 AI 带来巨大的生产力提升来“拯救”赤字,但这是否能实现仍是未知数。如果 AI 不能如愿带来生产力飞跃,这种无节制的支出将难以为继。
AI:不是泡沫,是残酷的“K型”清洗
手握 14 万亿美元资产的 Larry Fink 对 AI 的看法更为微观且残酷。他明确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在经历 AI 泡沫,但我认为会有巨大的失败案例。”
Fink 提出了“K型经济”的概念。他观察到,在各行各业,拥有规模优势的企业正在利用 AI 迅速拉开与中小企业的差距。他以沃尔玛为例,指出其利用 AI 进行库存控制和消费者偏好分析的能力已遥遥领先。
这种分化的根源在于令人咋舌的资本门槛。拉加德在现场透露,如今开发一个前沿 AI 模型的成本已高达 10 亿美元,且极度依赖跨境数据流动。而 Ken Griffin 则给出了更为宏观的数字:仅今年一年,美国用于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Capex)就将达到 6000 亿美元——Larry Fink 甚至在旁插话认为“实际数字会更高”。
如此高昂的“入场券”意味着,只有拥有深厚资本护城河的“规模运营商”才能玩得起这场游戏。正如 Fink 所言,AI 不会自然地“民主化”,反而可能加剧赢家通吃的局面。

关税回旋镖:谁在买单?
随着近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级,关税成为达沃斯论坛挥之不去的阴影。拉加德提供了一组令人咋舌的数据:美欧之间的平均关税水平已从一年前的2%飙升至目前的12%以上,且面临进一步上升至15%的风险。
“如果这些关税96%的成本都由消费者承担,这对通胀绝非好事,”拉加德警告。
Griffin则从微观企业角度痛陈关税的弊端。他指出,关税不仅是对消费者的累退税,更会滋生“裙带资本主义”(Cronyism)。在关税壁垒下,那些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公司将获得特权,而这正是扼杀中小企业创新活力的毒药。他提醒道,无论是BlackRock、Citadel还是如今的AI巨头,最初都是从中小企业起步的,保护这种市场活力至关重要。
央行独立性与“最后防线”
面对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市场往往指望央行再次“印钞救市”。拉加德对此态度强硬,她引用Paul Volcker的例子,强调央行必须保持独立性,不能成为财政政策的附庸。
“我不认为央行永远会是‘唯一的救世主’,”拉加德表示,单纯依赖货币政策无法解决结构性的财政失衡。
Tooze也补充道,央行独立性的概念本身就是1920年代为了应对民粹主义压力而诞生的产物,在当前极端政治化的环境下,保持央行的“防范道德风险”(Knave-proof)属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键。
世界经济论坛此次小组讨论全文:
达沃斯主持人 (Andrew): 非常荣幸邀请到这几位非凡的嘉宾加入对话。Larry Fink来自BlackRock,当然,他现在管理着14万亿美元的资产。我还应该提到,他是今年世界经济论坛的联席主席。在这段期间你做了非常出色的工作。

Ken Griffin也在这里。他是Citadel的创始人兼CEO。他管理着650亿美元的投资资本,并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处于金融业的前沿。关于经济走向,他一直是最具先见之明的人之一,我们稍后也会和他交谈。

然后我们邀请到了欧洲历史学家Adam Tooze。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的主任,著有五本书,包括《洪水:大战争、美国与全球秩序的重塑(1916-1931)》。

这就涵盖了我们要讨论的一些时期。稍后,拉加德也将加入我们,我们也期待与她探讨这个问题。但我想先从Adam开始,如果可以的话,请帮我们铺垫一下,为这一刻提供一些历史背景,因为这里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正在经历一次惊人的繁荣。其中一部分与技术有关。当时也有技术相关的问题,然后是各种货币问题,接着是稍晚出现的关税,你可以开始看到那看起来像什么样子。
Adam Tooze: 非常感谢。真的很高兴来到这里。我不认为我们应该做那种自动重复式的历史故事。我不认为历史是那样运作的。马克·吐温关于“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的名言很有用。我确实认为20年代有几个点与我们当前的时刻非常相关。一个是技术方面。那确实是一个新纪元的时刻,特别是在电力技术方面,还有大规模生产。那是福特的时代。
从本质上讲,那是福特主义成为全球现象以及一种社会模式的时候。这是一种高工资、高投入、高消费的契约,在最好的情况下,它稳定了高水平的消费和20世纪的增长模式。
但我认为更不祥的是,我们在谈论20年代时倾向于遗忘的一件事是,对于大多数同时代人来说,那是单极化的第一个时刻。那是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力量凯旋的时刻。为什么?因为自由主义列强赢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年代紧随一战这场史诗般的革命战争、第一场全面战争之后。而获胜的列强在某种意义上,在一段时间内,仍然掌控着局面。
Mark Carney昨天下午谈到的那个霸权的终结是谁的霸权?换句话说,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和美国,两个共和国,卓越的自由帝国力量,而俄国是他们唯一的盟友,却在1917年屈服于革命并成为了一个更激进的力量。他们权力的基础是金钱。是金融。是1920年代的美元霸权,本应锚定这个原本非常脆弱的世界。
20年代的启示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用技术和金融来稳定世界,但因凡尔赛和约及国联的失败而在政治上失败了。我们以为技术和金融会是一个好的替代品。在192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公式看起来是行得通的,因为最终金本位体系变成了一个日益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而傲慢、想象力的失败以及政治的失败,从未为那个结构提供支撑。但我没预料到在我的有生之年会有这样的时刻。这种经济力量、生产力量与对金钱(特别是美元)的依赖之间的差异,以及在这种背景下未能建立深层政治联系的失败,对我来说,这才是20年代的真正含义。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它在当前时刻如此引起共鸣,因为这里的关键力量是美国,20年代的关键力量也是美国。那些新技术是美国的。重要的金钱是美国的。而本质上正是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原因,违背了其霸权义务。
主持人:您在2024年秋天曾说,2020年代的AI泡沫与1920年代存在平行关系,即技术进步与全球贸易一体化挫折并存。希望您能详细阐述。

拉加德: 我想比较的是1920年代发生的技术突破。无论你看电网的规模和范围,看内燃机及其发展,还是看当时正在发展的装配线,那些都是那个年代发生的突破。与此同时,你也有一个表现非常好的股市。我们在20年代观察到的,也许Adam你讲过这一点,是全球贸易的重大变化。我不称之为崩溃,但它在大约几年内从占GDP的21%下降到了14%。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经济的飞速数字化,特别聚焦于人工智能。我们看到股市表现极好,不仅在发达经济体,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也是如此。我们看到了地缘政治的碎片化,这伴随着几乎所有产品类别的关税、进出口限制的增加。
这是前所未有的。只要WTO还在观察这些限制,我们还没看到贸易像我提到的数字那样崩溃。稍微下降了一点,但还在维持。问题是这能维持下去吗?但如果多给我一点时间,我想指出的关键点是:20年代和现在的一个大区别,这在某种程度上让当前的情况更加不可预测,可能也更加冰冷。我刚从外面的寒冷中回来。
“冰冷”是个合适的词。这个区别在于,1920年代的那些突破可以在国界内扩散——用通俗的话说。在那个年代,你未必需要那种规模和网络效应。
现在,如果你问数字化领域的巨头和人工智能的大金主们。顺便提一下,今天开发一个前沿模型大约需要10亿美元。如果你问他们需要什么,他们会说需要尽可能大的数据访问权。他们会说需要规模效应,以便真正摊销模型开发的投资成本。现在,如果我们因为世界各地不同的隐私法律和更多的保护主义壁垒而导致数据访问受限,那将会受到严重威胁,这将阻碍这些投资的规模化。
我现在可能对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持有过度消极和悲观的看法,但我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威胁。AI的发展,我们所希望的生产力收益,很难与标准、许可、访问方面的碎片化相协调。我认为这只能通过一定程度的合作来补救。这将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和容忍不同的范式、不同的文化偏好和不同的世界观。这很难。
主持人: Larry,如果你可以的话,请谈谈这个问题,因为我看得出你在思考。
Larry Fink:我认为对于西方经济体来说,如果我们不合作,如果我们不规模化,我们就会落后。我认为当人们问我“我们是否处于AI泡沫中”时,这将是压倒性的大事之一。会有一些大的失败,但我不认为我们处于泡沫中。但话虽如此,我更愿意说我们需要花更多的钱来确保我们能保持竞争力。
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每个人都相信AI会对信息产生巨大的J型曲线需求。关键在于确保这种需求只有在技术扩散到更多应用、更多用途时才会出现。如果技术只是六家超大规模企业的领地,我们将失败。所以对我来说,而且你知道,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信息。关键是我们扩散它的速度有多快,它被适应和采纳的速度有多快,对我来说这将是两个关键特征。对我来说,1929年演变进2029年的平行点是,对我来说限制因素将是:我们能否足够快地发展经济来克服赤字?特别是考虑到美国赤字的上升。第二,资本市场是否有能力继续资助这些投资以实现技术采纳的J型曲线?
主持人: 我想问Ken这个问题。1920年代有巨额债务资助了那个十年,你如何看待此刻的系统性风险、AI的集中度以及背后的债务?
Ken Griffin: 首先,很高兴参加这个“末日与阴霾”小组。1920年代的注脚是大萧条。我们此时此地的鲁莽在于世界各地政府的支出,它们都在入不敷出。这与1920年代私人资本市场的鲁莽不同。关于AI,巨大的问号是:它会创造出政府所期盼的那种生产力加速,以克服我们肆意的支出吗?世界需要一个救世主,希望在于AI。但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我们还不知道。
现在围绕AI有大量的炒作。在某种意义上,大型AI公司需要制造这种炒作来筹集进入该领域的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美元的投资。Larry可能在这方面(更清楚),但今年美国数据中心的资本支出大概是6000亿美元。
Larry Fink: 我认为会更多。
主持人: 但这是否意味着它被过度炒作了?
Larry Fink: 很多在建的数据中心是为了云服务。大问题将是支出的货币化。为AI建设的数据中心需要更先进的芯片。问题是那个芯片的寿命是多少?如果我们有新的技术变革,芯片的寿命只有一年,那么那笔支出将真的是一笔糟糕的支出。如果寿命像他们预期的那样是四五年,然后那些芯片可以用于云服务,那么我认为这些投资将被证明是好的投资。我个人对AI将如何影响世界非常乐观。
主持人:拉加德女士,关于当今系统中的公共主权债务。1920年代美国有预算盈余,今天有38万亿美元债务。我们从1929年后学到的剧本是用钱砸向问题。Ben Bernanke学到了这一点并在2008年实施了。我们在大流行期间又做了一次。下一次恐慌时,我们还能这么做吗?债券市场是否存在一条看不见的红线,投资者会说“我们不再买单了”?
拉加德: 我不否认对人工智能的投资可以是极度净正向的,并且会带来生产力收益,虽然其数量是有疑问的。关于它将带来多少收益,大家的看法跨度很大。
但我认为回到我关于“最低限度合作”的观点,我们也必须考虑到它是资本密集型、能源密集型和数据密集型的。我们必须注意这三者。就能源强度而言,使用什么样的能源来管理数据将很重要。这对人类会有什么后果也很重要。所以我认为在我们需要这种合作方法(包括处理数据隐私和世界不同角落的偏好)的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能源消耗、能源种类及其对气候的影响。
第二,我们必须注意这对人类的后果,因为除非你知道,我们进入凯恩斯的那个梦想世界,工作是一种选择——我在中期视野内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它对人类有什么后果,除非我们想冒社会混乱的风险。
回到债务问题,债务大幅增加,但关键是这些融资被用来做什么。投资于必要的生产性项目、出于安全目的的必要债务,总是会找到人来资助它。这是我的假设。那些不是用于生产性目的、不能在可持续基础上维持增长的债务,那将困难得多。所以我不会告诉你有一条红线。我也不会告诉你央行会永远在场。但我认为债务认购目的的性质将比实际体量更重要。
主持人: 关于央行可能并不总是会在场的想法,关于这点你知道些什么?
拉加德: 听我经历过很多危机,人们曾说“央行是唯一的救命稻草”,但这不是持久均衡的正确方法。财政当局必须采取措施,进行改革,并考虑支出的目的和对人民的后果,以维持社会团结。
Ken Griffin: 您是否在暗示,我们的立法部门已经放弃了财政审慎,变得过度依赖央行来应对鲁莽支出的冲击?
拉加德: 我不是暗示现在是这种情况,但在过去曾观察到过。
Adam Tooze: 历史的讽刺在于,20年代人们谈论央行是“唯一的救命稻草”时,是在敦促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问题在于我们有一个低通胀环境,增长停滞,包括贝莱德的知名人士都在主张更自信的财政政策,因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杠杆之间存在深刻的不平衡,这也是1920年代的一个教训。
而现在,正如Ken所暗示的,你所主张的,我理解是一个更抽象的主张,即每个政府部门都有责任。是的,这种责任不仅涉及宏观总量,我听你说,还涉及具体的支出类型。你对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区分,不仅是出于经济目的,也是为了政治合法性和社会一致性这一关键问题。因为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契约,但实际上在欧洲,正受到一种观念的深刻压力,即现代福利国家是非生产性的,以及大量的非常恶毒的分配斗争,这正在唤醒另一个1920年代的幽灵,即法西斯主义的幽灵,对吧。那种某些与会者很想让我们给更多平台的政党,他们是那种传统的直接继承者。他们现在正在欧洲动员起来,围绕着取消公共支出的合法性,攻击这些生产性的、非生产性的、国家的、国际的、移民的、种族的、国家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政治具有爆炸性。
Larry Fink: 但是Adam,在2000年代,“大而不倒”这一信条(Andrew写过的),但因为“大而不倒”的信条,有一种社会观点是:不要救助。所以没有像必要的那样多的财政刺激。但我会说,从中吸取的教训是2020年,你可以争辩说我们使用了巨量的财政刺激,可能太多了,你知道回过头来看。所以我实际上相信,你知道,我们都在进化,我们在决定拉哪个杠杆。所以我认为你知道,欧洲,特别是在2008和09年之后,可能没有使用足够的财政手段。我们都在进化,在决定拉动哪个杠杆。
Adam Tooze: 这也在于你有什么样的结构。再次强调,因为欧洲人有工作,他们本质上有短时工作制度,让人们保持就业。而美国,在2020年失业率飙升,没有真正的国家失业保险系统在运作,不得不依赖这种“虚假繁荣”的万亿美元支票寄到邮箱里的紧急救助美国社会的方式。这很容易做过头,但这确实是近代伟大的宏观经济成功故事之一,我们没有再发生一次1929年。
主持人: 拉加德女士,关于央行相对于政治阶层的独立性。在危机期间,央行行长必须与政府合作。您最近签署了一封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信,您怎么想?
拉加德: 不,但这……不,但这触及了一个有趣的平行点。这触及了一个有趣的平行点。如果你回去看看1920年代特别是1929年实际发生了什么。我读过那个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的一些日记。他们非常担心当时的政治。他们对政治非常认知。顺便说一句,并不是那时的总统,也就是胡佛总统,在告诉他们确切要做什么。而是他们担心央行本身会……这在那时被认为仍是一个实验。它仍然是新的。
Larry Fink: (会被)解散。
主持人: 你会谈论央行行长是否还会在这里,他们不确定什么,他们不确定是否会打破平衡,国会是否会说,受够你们了。所以我想知道,在这些危机期间,也有很多时候央行行长必须与财政部和总统携手合作。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刻。你最近公开站出来。你知道,签署了一封关于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美联储的信。你是怎么想的?
拉加德: 首先,我要区分……向你的工作致敬,因为你真的非常详细地研究了他们在那些日子里是如何思考的以及他们的恐惧是什么。但我会区分今天那种“携手合作”——我们在新冠期间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做的,面对现实吧——与“财政依赖”。所以在特殊情况下携手合作,哪怕那是极其特殊的,我认为是完全合法的。是否做得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应该,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辩论。
它采取了什么形式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在大西洋这一边的震荡吸收器和直接给消费者的财政支出之间,我认为你知道,关于哪种最有效尚无定论。但财政依赖是另一回事,我强烈反对。你知道,对我来说,打破这种央行行长依赖性的伟大冠军和英雄是Volcker。他冒了风险。
巨大的风险,真正影响经济,危及经济,以确保持久的价格稳定。我认为当时他在尼克松总统面前的立场,为了展示央行的独立性以恢复价格稳定,这是我们应该,你知道,记在脑后的一件事。我不打算评论就在现在发生的事情,包括今天,实际上。只要说,我和其他几位同事确实采取了主动,在一周前发生的事件背景下,主张央行的独立性。
Adam Tooze: 真正令人着迷的事情之一是,央行独立性的概念本身就是1920年代的产物。它是1920年代的产物,因为大多数央行,不像美联储,是古老的机构。像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他们在20世纪初必须应对的是现代民主的出现,即多党制、民粹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右翼分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联储在某种意义上生于危机之中,美国没有更早建立央行的原因之一是它是一个民主国家,而资本主义民主是充满争议的,金钱在资本主义民主中是充满争议的。央行也是极具争议的,美国直到威尔逊在1913年达成妥协才实现这一点。而其他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当然,必须真正弄清楚在一个实际活跃的社会民主制度中,做一个以市场为中心、以金融为中心、作为银行的银行意味着什么。正是从中,这种概念从一开始就对民粹主义民主充满敌意,从1920年代开始就是这样。
那句话是Montagu Norman的话,“防范道德风险”(Knave proof),对吧?你想让央行制度能够防范那种压力。在当前时刻这有某种共鸣,对吧?你需要使央行机构能够防范那种政治压力。我认为自Volcker以来,这一直是思考专业知识、政治和市场压力之间关系的一个富有成效的场所。人们可能对Volcker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他设定了现代独立央行的范式,无论人们是否喜欢这个范式,但这显然是卡特到里根时期的定义性时刻,顶住了里根总统任期内的压力等等。但是……
Ken Griffin: 只是为了把事情放在背景中。现代央行代表了我们不在金本位上的现实,那是我们在越南(战争)时期的……
Ken Griffin: 回到150年前。我不是主张我们应该实行金本位,只是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然后今天和回顾100多年前的第二个显著区别是债务无处不在。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如果你有……
主持人: 哪里有债务……
Ken Griffin: 无处不在,通货紧缩。
Adam Tooze: 他的……很害怕。好吧,这就是现实。在一战后的20年代,债务也是无处不在。一战后欧洲的债务对GDP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一战后没人实行金本位。所以实际上,他们必须管理民主,处理140%、150%的GDP债务,并弄清楚你要怎么做中央银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选择了金本位。所以当时英国、法国、德国,没有一个在实行金本位。还有1919年的意大利,当20年代开始时,他们都必须通过与美国的趋同回到那里。这成为了1920年代凯恩斯和温斯顿·丘吉尔之间的大冲突:我们将付出什么代价?这是黄金十字架(Cross of gold)。在美国是William Jennings Bryan。在欧洲的1920年代。我们将为重新稳定付出什么代价?这就是让它看起来、感觉起来像20年代糟糕的欧元区的原因。
拉加德: 对?但这在当时和现在之间也是一个巨大的区别。
拉加德: 货币政策结果完全僵化,而我们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
Ken Griffin: 还有大量的成功故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看欧洲的价格稳定,我不想乌鸦嘴,但现在看起来真的很不错。
Larry Fink: 是的,我想把它带回今天和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我认为这是我们思考2026年世界经济论坛和达沃斯的基础。那就是技术将如何重塑社会的许多部分,无论我们是否把数据搞对。我从贝莱德的视角看到的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行业出现K型经济。是的,一个巨大的超级赢家和许多输家。几乎每个行业的赢家都是规模运营商,他们有机会、内部现金流、盈利能力来更快地利用AI。以沃尔玛为例,他们对库存控制有着极其出色的知识,这几乎超越了任何其他零售商。当消费者买东西时,当东西从货架上拿走时,他们立即了解消费者的偏好,他们可以导航一家店对比另一家店。你在他们的业绩中看到了这一点。你看到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一个季度接一个季度地表现出色,获得更高的回报,而此时很多零售商真的很挣扎。我们有破产资产等等。我在每个行业都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可能会在每个国家看到这一点,现在的规模运营商正在获胜,这并没有转化为世界经济的广泛化。在许多方面,它可能正在变窄。对我来说,这回到了拉加德所谈论的,我们能多快看到AI和技术的适应和民主化将是真正的关键点。AI能足够便宜吗?足够普及吗?以便它可以分布到小企业、中型企业,它们可以成长并拥有与规模运营商相同的优势。
但在这段时间里,规模运营商正在获胜。我的意思是,我在资产管理行业看到了这一点,规模运营商拥有更好的连接,因为利用了更多的技术。我认为这只是在初始阶段,这将代表一些巨大的社会问题。
主持人: 我可以稍微转换一下话题,抛出另一个实际上并未发生在1920年代,但在技术上发生在1930年的大问题,我认为这在每个人心中都非常重要,谈论平行线,那就是在1930年,胡佛总统,他在1928年为了赢得选举非常渴望获得选票,为了从农民那里获得选票,他向他们承诺他将实施关税。1930年到了。我们已经经历了1929年的崩盘。每一位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都跪着去华盛顿说,请不要这样做。我求你,不要实施这些关税。当然,因为他为了获得这些选票做出了这个承诺,他说他需要推进它。然后当然,一年后,贸易下降了60%。
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在现在的背景下思考这个问题的。我想总统今天晚些时候甚至可能会谈论关税。而且不仅仅是关于那一刻贸易下降60%发生了什么,还关于实际上花了多长时间,因为政治原因,才有效地解除那些关税,并把我们带入一个更全球化的秩序,而这在这个特定时刻可能会被解构。谁想回答这个问题?
Adam Tooze: 我的意思是,我听到Larry的暗示,不要再多谈历史了。所以我要转向现在,说最大的区别是这个关于法币的问题。因为真正导致30年代初全球贸易崩溃的是关税与货币混乱的结合,1931年金本位的崩溃,然后是引入大量的配额。在当前时刻,我们距离那样的世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尽管这些很糟糕,但这看起来更像是经典的贸易战类型的关税。这不太好,特别是考虑到当下关税制度的波动性。这才是真正让它变得奇怪的地方。历史上就是这样,我们实际上不知道下周美国的关税会是多少。但这,我认为是一种相对的安慰。这是我不认为有理由恐慌的一个轴心。
主持人:拉加德女士,你是否认为这些关税是一种永久状态?如果我们20年后坐在一起,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关税会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吗,以及我们全球面貌的那种分裂。
拉加德: 我当然希望不会。但是让我们看看,20年后,你可能在这里,我可能不在。但是,你知道,再次,我认为重要的是深入那些关税的表象之下,看看是谁在承受冲击。我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你知道,我没看到很多研究,但在德国基尔研究所肯定有一项研究,认定美国消费者和美国进口商是关税负担的主要承担者。如果我现在看美欧关系,从2%的关税,但是一年前,我们现在在欧元区的平均关税是12%点多。随着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有针对性地话,我们将平均上升到15%。如果那其中的96%是由美国消费者和美国进口商承担的,那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结果,特别是在通胀方面。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真正深入研究后果是什么,溢出效应是什么,结果导致的通胀结果是什么,以及增长如何受此影响。
Ken Griffin: 所以我,你知道,显然,我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这个话题发表过言论。遗憾的是,我认为我强调的一些担忧已经成真了。关税对美国消费者是累退的,我们看到政府取消了对直接触及美国消费者的商品的关税,不是所有商品,但他们取消了很多商品的关税。第二是谁为关税买单,对吧?对于任何税收,关税就是一种税,总有一个问题是谁支付税款。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有两三个研究已经完成,表明这种税的归宿落在了美国消费者和美国公司身上,而不是外国公司。然后,当然,裙带关系(Cronyism)是关税带来的持续恐惧,你创造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公司是那些讨好欢心的公司,这让中小企业处于真正的劣势。
我要触及这里的一个点,回到你关于这些非常大、成功的企业崛起的评论。它们大多数是在我们有生之年作为小企业起步的,对吧?我右手边的人经营着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他创办了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并在不到一辈子的时间里创造了那项业务。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
这是美国经济活力的故事,中小企业在短短几十年内就能崛起成为全球领导者。事实上,如果我们看今天的AI公司,每个人都在谈论Anthropic和OpenAI。Anthropic几年前还不存在。OpenAI 15年前也不存在。英伟达是一家制造视频游戏处理器的公司。AI领域最大的三个心智份额名字实际上都不到大约10岁。正是这种活力吸引资本来到美国,确实让人感受到美国经济的繁荣。我们需要继续保护我们中小企业的机会集,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哪一个会成为下一个BlackRock,下一个Anthropic,Apple等等。
主持人: Larry,我有一个技术问题问你。我们在1929年确实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实际上是技术。你的意思是纽约证券交易所无法跟上交易量,事实上?我的意思是,你看到那些著名的黑白照片,成千上万的人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那是1929年10月的崩溃过程。他们站在那里是因为他们试图找出他们的钱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道,因为处理太滞后了。今天,我们可以在手机上获取这些信息,精确到毫秒,几乎完美。
然而与此同时,谈谈谣言可以传播并且传播得很快的想法。你知道,在旧时代,某种坏谣言传播需要很长时间。然后顺便说一句,从效率上讲,纠正那个谣言也需要很长时间。但今天,我们在美国的硅谷银行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当有人说并公开说,“我要把我的账户从这家银行转走”的那一秒,每个人都可以冲向出口。因为他们可以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到这一切,所以虽然技术在一方面是了不起的,我想知道你认为另一方面的风险是什么。
Larry Fink: 所以我会争辩说,通过透明度,实际上风险更小。我认为硅谷银行是一家监管不力的银行。我的意思是,实际上,贝莱德被要求对他们的资产和负债组合进行研究,我们在它倒闭前两年确定它是当时美国错配最严重的银行。所以我认为那是监管的失败,而不是信息的传输。
我真的相信,当你谈论其他事情时。我的意思是信息的传输是经过处理的。是的,我们在任何一个给定时间都可能有相当极端的日常波动。但我们在2025年都忘记了一件事。如果你选每个季度的第一天,10年期国债移动了3个基点。这就是它们所做的全部,1月1日,你知道,4月1日。然后10年期国债移动了三个基点?是的。但在那些季度之间,有巨大的波动,你知道,而且……但这正是市场的效率。这是Citadel创造的美妙之处,资金的快速移动使其平衡,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确定什么是公允价值。我认为那是资本市场的宏伟之处。
透明度是引擎,我会说。市场运动的引擎,Ken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是这方面架构的天才之一。
但我会说,回到技术上一秒钟,是的,我认为向代币化、十进制化的移动是必要的。讽刺的是,我们看到两个新兴国家在十进制和货币的代币化及数字化方面领先世界,那就是巴西和印度。我认为我们需要非常迅速地朝那个方向移动。我们将减少费用,我们将通过减少更多费用来进行更多的民主化。如果我们所有的投资都在一个代币化平台上,可以从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移动到股票和债券并来回移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区块链。我们将,你知道,我们可以减少腐败。所以我认为,是的,我们可能对某一个区块链有更多的依赖,我们可以讨论这个。但话虽如此,这些活动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理得更安全。我们……
主持人: 我们要超时了。Ken,非常快地。当你现在思考这其中的技术部分时。我想你认为这对社会来说利大于弊,但我确实想知道你是否认为技术部分代表了我们应该思考的风险。
Ken Griffin: 我们的金融市场的技术还是技术……
主持人: 宏观上的技术。我的意思是,我认为金融市场因为(技术)安全多了。
Ken Griffin: 看,有一个简单的,你知道,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历史时刻有多困难。好吧,你可以过你今天拥有的生活,或者出生在200年前做英国国王。你更愿意拥有哪种生活?
主持人: 好的,在历史上,你认为我们真正处于哪一年?最接近的类比是什么?
拉加德: 你知道,我想起了汉密尔顿对乔治国王的一句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想这就是我们都想知道的,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我认为我们都对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负有责任。而我的“最低限度合作”就是我现在要摆在桌面上的恳求。